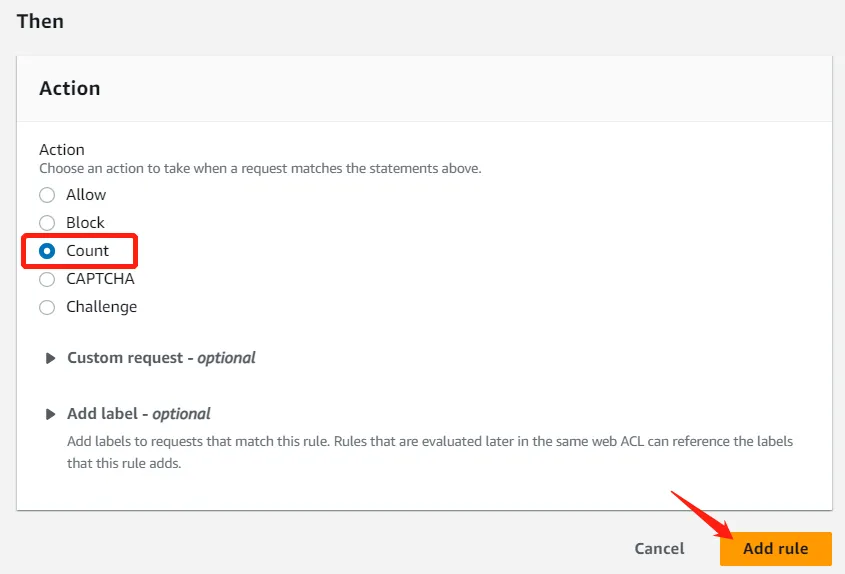李飞飞:是李井泉的孙女吗?
李飞飞:是李井泉的孙女吗?
李飞飞的简历堪称辉煌:她在33岁时成为斯坦福大学的终身副教授,并成为首位担任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的女性。她不仅是美国三院院士,还是现代人工智能的催化剂之一,ImageNet的创建者,曾担任谷歌副总裁以及谷歌智能云和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的首席科学家。
在一个长期由男性主导的人工智能领域,李飞飞的开创性成就显得尤为突出。人们对她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贡献感到钦佩,同时也为她的逆袭故事深受感动。她在成功之前,曾经历过艰难的青少年时期:她在学校里表现出色,但受到老师的性别歧视;初到美国时,她的英语不流利,家庭经济拮据,且母亲遭遇健康问题;在求学过程中,她也曾面临科学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艰难抉择。
这位华裔移民少女是如何突破美国社会的阶层限制,成为全球深度学习革命的引领者的“AI 教母”?
(下文摘自《我看见的世界:李飞飞自传》,中信出版集团 2024)
“我不禁回想起第一次来到华盛顿时的情景,那时我对人工智能一无所知,也未曾进入学术界,更与硅谷没有任何联系。那时我在外部世界的身份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便是——移民。和许多移民一样,我感到自己被复杂的文化鸿沟所隔绝。某些鸿沟不可言喻,而另一些则清晰可见,难以跨越。我是一名女性,而我的研究领域却是男性的天下,科学界的典型形象一直是“帽衫男”,以至于这个词现在已没有讽刺的意味。这些年我常常思考,自己到底属于哪个世界。”
父母播下的种子
我出生在北京,但成长于四川省的省会成都。尽管这里名义上是母亲的家乡,但她和家人在此定居的时间并不长。他们原籍杭州,在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杭州沦陷,他们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被迫离乡。他们虽幸存下来,却无法摆脱流离失所的痛苦,母亲这一代人也深受其影响。
外祖父常常怀念动荡前的岁月,每当提起,便感到无比痛心。他在学校表现优异,本有美好的前途,却因养家糊口而不得不放弃。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陷入了长年的贫困之中。几十年来,外祖父郁郁寡欢,难以释怀,这种情绪也传递给了他的子女,最终也影响了我:一种沉重而默然的情感,仿佛家在他乡、生活在别处。
在我心中,父亲是理想的父母形象,然而这也表明了我对他的严厉批评。
他的外表英俊整洁,性格上却对任何严肃事物都心存抵触,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他终生如孩童般生活,对成年人的责任无所顾忌,似乎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已成人,缺乏其他人天生的基本感知力。他常常突发奇想,随心所欲。
在母亲生产的那天,父亲却因去公园观鸟而姗姗来迟,完全忘记了时间。这次的迟到令他想到了用“飞”字作为我的名字,于是“飞飞”便成为了我名字的选择。
这个名字恰好是男女通用的,反映出父亲对性别这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概念的无所谓。此外,我们这一代人中很少有人叫“飞”,正好契合了父亲标新立异的风格。
在我的童年,父亲常常用各种零件自制自行车,带我穿过拥挤的成都街道,带我去公园或乡村。我们会花上几个小时捉蝴蝶,观察水牛悠闲地躺在被水浸泡的稻田里,或是捕捉野生动物和竹节虫,将它们带回家当宠物。
外人也能明显感受到,我们之间并没有传统父女间的等级关系,父亲更像我的同龄人,而非父亲,这使我看不到为人父的压力与焦虑。
父亲那种乐在其中的专注状态让我明白,无论他有女儿、有儿子,还是根本没有孩子,他都会如此度过午后时光。正因如此,他成为了我心中极具感染力的榜样。无意识中,他向我展示了最纯粹的好奇心。
父亲带我出去玩,不是为了教我什么——他虽然热爱自然,但并非专家——然而这些经历在我心中播下了探索的种子,成为塑造我人生的最大动力:对未知事物永不满足的渴望。
若说我强烈的好奇心源自父亲,那么指引我这份好奇的人便是母亲。
母亲的个性同样源于自我认知与社会期待之间的矛盾。她是困囿于平庸生活的知识女性,但意识到想象力并非受现实限制,因此自小便沉浸在书海之中。阅读为她打开了一扇窗,让她了解无法亲身经历的生活与时代。
她热切地与我分享她对书籍的热爱,鼓励我广泛阅读各种类型的书籍。因而,我不仅熟读鲁迅的作品和《道德经》等道家经典,还阅读了《第二性》《双城记》《老人与海》《基度山伯爵》等西方经典的中文译本。
外祖父母的培养方式与父母的价值观不谋而合。他们并不认同重男轻女的观念,而是鼓励我展开想象,坚守原则:我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其次才是女孩。像母亲一样,他们常为我购买涵盖海洋生物、机器人和中国神话等多元主题的书籍。
直到长大后,我才意识到,家门外的世界或许更加复杂。
科学是男孩的游戏?
美好的校园学习时光在一个下午戛然而止——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在小学的最后一年,老师在下课时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女生先回家,男生则在座位上多坐几分钟。我顿时好奇,便藏在教室门口,能听到老师说话,我所听到的话让我终生难忘。
“我让女同学先走,是因为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的整体表现是不及格的。男孩天生就比女孩聪明,数学和科学是你们才能的基础学科,为什么你们的平均成绩竟然比女生还差?我今天非常失望。”
接下来,她似乎认为有必要鼓励大家,语气稍微缓和:“不过,也不要自暴自弃。等你们到了十几岁,周围的女生自然会变笨,她们会不断退步。即便如此,我希望你们能更加努力,发挥你们作为男生的潜力。落在女生后面是不可接受的,大家明白了吗?”
我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脑中冒出无数问题:老师真的相信男生天生更聪明吗?女生真的会长大后变笨吗?难道所有老师都是这么想的吗?她居然是个女老师!
经过一段时间后,诸多疑问被另一种感觉所取代,这种感觉沉重而强烈,仿佛从我内心深处升腾而起。这种感觉不是气馁,甚至不是被冒犯,而是愤怒。
这是一种不熟悉的愤怒——一股悄然而炽烈的怒火,一种我在母亲身上见过的愤慨,但它无疑属于我自己。
老师的这番话并不是性别歧视的首次迹象,大多数迹象隐晦而难以察觉,我感到在数学和科学方面,老师更愿意鼓励男生。
有些区别对待则显而易见。例如,我曾报名参加一年级的足球比赛——不是“男队”,而是校队——结果却被告知女生不能参加。
老师的话让我震惊,却并没有令我气馁。相反,这些话强化了我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理念:无论面临多大障碍,都要奋力超越现状,构想出更加辽阔的未来。若数学与科学是男孩的游戏,那么又如何?学习毕竟不是比赛,他们无法阻止我参赛,我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赢。
后来,我进入了一所吸引全市优秀学生的中学。在那几年里,关于女孩的偏见让我愈发不满,这种情绪超出了学业的范围。
在同龄人中,我已获得“假小子”的称号,然而老师的话仍在我脑海中回响,使我将最初的怪癖上升到了个人使命的高度。
像任何愿意将生活视作电视剧的青少年,我很容易认为在与中国性别规范抗争的过程中,自己是孤军奋战。我剪短头发,拒绝穿裙子,和一群骑单车、爱打闹,聊战斗机而非校园八卦的男同学们打成一片,全身心投入那些出乎意料的兴趣中,特别是航空航天科学、高超声速飞机设计,以及不明飞行物等超自然话题。
母亲是我坚实的守护者。当她觉得自己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受到质疑时,她毫不犹豫地反击。我的中学老师体验过她的厉害,而那次令人难忘的会面,似乎直接改变了我的命运。
“您女儿特别聪明,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我担心,她对自己的未来不够重视。比如,期末考试越早准备越好。我经常要求每个学生分享他们正在读的书。大多数同学分享的都是教科书、备考资料和学校推荐的书目。但是,飞飞这周推荐的书让我很担心……”
老师未说完,母亲便插话:“我女儿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她对老师的轻视态度显露无遗。
“问题出在她读的书上。你看看,《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勃朗特三姐妹的书?以及她订的这些杂志,关于海洋生物的、战斗机的,还有不明飞行物的……举不胜举。她没有重点阅读符合课程价值观和理念的文学作品。”
“是吗?所以呢?”
沉默片刻,我坐在母亲身边,努力抑制内心的喜悦。紧张的气氛持续了一两分钟,随后老师向前倾身,做出最后一次努力,语气中带着几分严厉。
“我直说吧。您的女儿也许真的挺聪明的,但班上聪明的学生可不少。智力只是成功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纪律性,要将个人兴趣放到一边,专心学习对未来最有用的东西。”
我不确定母亲接下来的话是否是回应。她低下头,声音比之前更轻:“这是飞飞想要的吗?这是我对她的期望吗?飞飞,你和我一样,都不属于这里。”
1992年,我刚满15岁,父母带我来到美国的新泽西州定居,改变开始了。
十字路口的抉择
得知我获得普林斯顿大学近乎全额奖学金录取时,母亲表现得十分淡定,几年后我才真正理解这一刻对她与家庭的重要意义。
母亲生命中的每个里程碑都提醒着她,自己站在了无法弥合的鸿沟一边。几十年来,她已习惯伪装自信,但我知道,她从未真正感到过自信。如今,也许是人生第一次,她终于有理由相信这个故事并非简单。她为此全力以赴,终于感到一丝轻松。
直到1999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学习即将结束,再次面临科学理想与现实生活的抉择。读研的诱惑与开启职业生涯的压力让我左右为难。这是一个真正的两难困境:
母亲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经营洗衣房的劳累与家庭的债务给她带来巨大压力。而华尔街的公司可以提供一切:福利、晋升机会、令人艳羡的薪资,当然还有真正的医疗保险。他们愿意承担我们的债务,并为我的家庭提供保障,而要求我放弃科学。
“飞飞,这是你想要的吗?”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妈妈。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面对我的含糊其词,母亲的回应总是直击要点,速度之快让我稍作愣神。三步绝杀,一剑封喉。我决定去读研究生。
然而两年后,坏消息再次降临。选择神经科学与计算科学的研究生课程已让我身心疲惫,而此时得知母亲患上充血性心力衰竭,我的感受复杂得无法用语言表达。
新的现实正在出现,复杂得动摇了我从物理学专业生入学普林斯顿以来做出的每个决定。毕生的好奇心将我引入一个竞争激烈、薪水低廉、无法保障职业生涯的领域,而我的父母现在需要我无法提供的支持。
我每天都在追逐自己的梦想,这让我感到极度自私,甚至过于鲁莽。我的实验室伙伴大多来自中产阶级,有些甚至家庭富裕。越是反思与他们的差距,我越难否认:成为科学家是一种奢望,我负担不起。
几周后,一位同学提到,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合伙人来招聘。他们在寻找实习级别的分析师,常春藤盟校里与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有一点联系的研究者都可成为理想候选。这似乎成为了绝望时刻值得考虑的机会。
当然,我以前也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我的学术目标与现实生活间的冲突一直存在,我很想将这次事件视为最近的一次小冲突。但这一次,我内心的科学家声音与以往不同。在母亲健康遭受新一轮打击后,它变得不再坚定,甚至我内心那份特殊又戒备的情感也开始屈服。
面试后,麦肯锡公司立即给了我肯定的回复,决定将我的实习机会转为正式职位。
我心中五味杂陈,难以言表。一方面,我将要放弃我所研究与热爱的全部,另一方面,我亲眼目睹父母多年来的窘迫,越发觉得他们为了我做了巨大的牺牲。这份工作似乎让我终于可以卸下肩上的重担,为了让我来美国,母亲已付出了所有。我知道,现在是她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向母亲讲述了面试、工作机会等一切,告诉她待遇、起薪,以及在我还未答复前,他们就已提出了优厚的条件。我解释说,从各个角度看,这都是通往每个移民母亲所希望自己孩子拥有的职业生涯的捷径。她礼貌地听着,但我未说完,便看到了她脸上那种熟悉的神情。
“我们真的要再次讨论这个问题吗?我了解我的女儿。她不是管理顾问,或其他什么职位。她是科学家。”
“想想你的身体吧,妈妈!想想我们的开销。搞学术能带给我们什么呢?”
“飞飞,我们走到这一步,不是让你现在放弃的。”
“这不是放弃!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一份事业,可以让我们摆脱目前的困境。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三个大人住在一个宿舍里!”
母亲沉默片刻,似乎在思考我的话,随后回答:“飞飞,你一直说自己走的路很‘自私’,仿佛追求科学是在牺牲我们。”
“我怎么能没有这种感觉呢?我本可以养活我们所有人,而且……”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这从来就不是你一个人的路。从一开始,这就是我们全家的路。不管你注定要成为科学家、研究员,或其他我无法想象的职业,也不管你能否从中获利,从我们离开上海的那一刻起,我们全家就朝这个目标努力。”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再说最后一次:我们走到这一步,不是让你现在放弃的。”
她是对的。她总是对的。这一次,不知为何,我终于听进了她的话。从此我再未质疑自己的道路。
她们,同样属于这个时代
2015年,图像分类虽然已成为老生常谈的技术,但技术接连发生失误:将达豪集中营大门的照片标记为攀爬架,将一位脸上涂有彩色粉末的白人妇女贴上“猿”的标签。虽然事故并非恶意,但这并没有让人感到宽慰。事实上,无心之失所揭示的问题更令人不安:包括ImageNet在内的数据集因缺乏多样性,导致了一系列意外后果,未经充分测试的算法和存疑的决策进一步加剧了负面影响。在互联网主要展现白人、西方人与男性生活图景时,我们研发的技术确实难以理解其他人群。
正如记者兼评论员杰克·克拉克(Jack Clark)所言,问题的根源在于人工智能的“男性之海”:科技行业的代表性不足,导致算法无意间带有偏见,在非白人、非男性用户身上表现不佳。
从代表性问题的出现到受到大众真实感受,往往需要数年。因此,我与几位伙伴联合创立了非营利教育组织AI4ALL,旨在推动针对高中女生、有色人种和其他未被充分代表的群体,开放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课程,提升STEM(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领域的包容性。
这一小步虽微不足道,但我们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飞跃。只需一点点努力,就能让每一个长期被历史排除在外的人相信,她们同样属于这个时代、这个领域。
此外,项目还带来一丝安慰——在业界追逐人工智能未来时,往往缺乏自省,而我们的努力能够确保,至少有一小部分人在逆向而行。
2016年,我迎来21个月的学术休假,决定暂时离开教授职位。经过深思熟虑,我最终选择接受谷歌云的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一职。我约有幸认识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黛安娜·格林(Diane Greene),她是少数征服硅谷的女性之一,我期待能在性别比例极不平衡的行业与她并肩作战。
回顾我的职业生涯,这段漂洋过海的经历深刻影响了我。然而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这种影响一直延续着,塑造着我的研究与思考:最佳作品总是在边界上诞生,于此,思想在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之间徘徊,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但这正是我们如此强大的原因。独特的身份赋予我们独特的视角,以及挑战现状的自由。
作为女儿、科学家、移民与人道主义者,我见证了众多不同的世界,但最重要的世界是我将不会生活的世界,是建立在我当前所做一切之上的世界,是我倾注所有爱与希望的世界,也是我最为感激的世界。正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存在,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才有意义。这个世界是我孩子们及他们的孩子们将继承的世界。在人工智能时代,做母亲是我最谦卑的体验,我相信,这也将永远是独属于人类的体验。